![世界文学名著《父与子》(pdf电子书下载)[s2078]](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2024/04/451.webp)
译 序
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ABCDEFGHFFBIJ
KLGHFDFB,一八一八——一八八四)是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
艺术大师。他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
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
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屠格涅夫生于奥廖尔省的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夫村
的地主庄园,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八二七——二九年就读
于莫斯科的一个私立寄宿学校。一八三三年入莫斯科大学,翌
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一八三八——四二年在德国柏林
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一八四二年回乡,但后又曾长期出
国。
屠格涅夫从《巴拉莎》(一八四三),《地主》(一八四六)等
诗篇开始文学生涯。他的《猎人笔记》(一八四七——五二)的
发表曾当作俄国文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篇篇特写,以俄
国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广泛地描绘了庄园地主和农
民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
的本性,全书充满对含垢受辱、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
当时的进步思想界称它是对农奴制的“一阵猛烈炮火”,是一
部“点燃火种的书”。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
逝世,实质上则因其《猎人笔记》的社会思想倾向而被捕,送往
1父与子
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夫村软禁。软禁期间他写了中篇《木
木》,以满腔仇恨对农奴制进行控诉。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他创
作最旺盛的时期,适逢俄国社会运动逐步高涨,他及时地反映
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长篇《罗亭》(一八五六),《贵族之
家》(一八五九),中篇《阿霞》(一八五八),《多余人的日记》(一
八五○)展示了贵族知识分子言语脱离行动,理论脱离实践的
一些典型特征。长篇《前夜》(一八六○)则反映俄国农奴制垮
台前夕在俄国出现的进步社会思潮。在屠格涅夫创作中占有
中心地位的长篇《父与子》(一八六二)刻画了两种社会势力
——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派贵族间的思想冲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作家本人在两派思想冲突中转向
了自由主义者一方,与他常为之撰稿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刊物
《现代人》决裂。他转变后的思想流露在一八六七年写的长篇
《烟》里,他以同等的否定态度描写了反动贵族和革命运动参
加者。最后一部长篇《处女地》(一八七七)是有关七十年代俄
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晚期作品《散文诗》(一八八二)的内容和
倾向呈现出多面性,既有悲观情调也有乐观情调,既有抒情也
有讽刺。屠格涅夫还写有剧本《食客》(一八五七)和《乡村一
月》(一八五五)等。
屠格涅夫文笔婉丽,结构巧妙,语言清新简洁,深得读者
喜爱。其作品很早就有人译介,译介者有老一代知名作家,也
有我的同时代人。
屠格涅夫创作《父与子》的那些年月,农奴主已不再可能
一成不变地维护自身的统治,农民贫困日益加深从而使他们
2父与子
有了独立自主地走向历史前沿的可能性。然而此种形势转化
为革命尚缺主观条件,数百年来受农奴主奴役的人民还没有
能力站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作广泛的、公开的、有意识的斗
争。
屠格涅夫作为当时启蒙思想的代表,对专制的农奴制及
其经济、法律、警察制度深怀不满;他主张普及教育,实行自
治,全盘欧化,他主张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最主要是农民的
利益。
如上所述,屠格涅夫属俄国社会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一翼。
按他自己的解释,“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自由主义者’是指
反对一切黑暗和压制,尊重科学和教育,热爱诗歌和艺术,首
先则是热爱人民的人……”他赞赏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们
为事业善作奉献的平民精神。然而他与社会运动的另一翼
——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张“渐进”,他认为另一派只是唐
·吉诃德悲剧式的、缺乏现实生活感的人,他喜欢温和的君主
立宪而不喜欢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
“庄稼汉民主”。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里。
但屠格涅夫是个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必然把历史的
重大客观事件置于视界之内,把再现生活作为无可推卸的责
职,去塑造符合时代的典型。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
主启蒙时期否定精神的一个很有特性的表达者:“我们认为有
利,我们便据此行动……现时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们也去
否定。”作者认为社会在变革时期总会伴随某种偏向,否定精
3父与子
神在社会变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无情的,具有破坏性的,但
到后来,在社会经过变革以后,便会褪去破坏性的色泽。否定
的结果将是肯定,因为新事物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
身的发展。
毫无疑问,巴扎罗夫反映了进步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想法。
屠格涅夫在给他的朋友、俄国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道:
“他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其实应该读成革命志士。”巴扎罗夫
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争论时,态
度凛然地要求对方“那怕举出一件当代生活中的,无论是家庭
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罗夫,他理解到,为使新生事物取得胜
利,否定是种有效的武器,它具有历史意义。作者善于捕捉十
九世纪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进思想萌动,他看到了否定
派即虚无主义者“对人民的需要更为敏感”(作者语),他们的
心曲与人民有互通之处。巴扎罗夫反驳帕维尔·基尔萨诺夫:
“您不赞成我的选择,但谁对您说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时心血来
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种过
地,您去问你们的任何一个农民,看他首先认作同胞的是您还
是我。”书中形容巴扎罗夫“仆人对他几乎都有好感,尽管有时
要挨他的取笑,他们觉得这人不是老爷,而是自己人”;“他有
一种使下人信赖的特殊本领,虽则从不迁就他们,说话的口气
也是懒懒的”。所有这些素质,都为作者所肯定,所珍视。
但作者笔下的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否
定一切”,但在建设方面,据巴扎罗夫的话说,“不是我们的事。
首先要把地面打扫干净。”他无疑带有左倾无政府主义极端
4父与子
性。在作者笔下,虚无主义者有着对一切进行无情地破坏的自
发性,他们想法片面,老是怒气冲冲,脸色阴沉。屠格涅夫描写
巴扎罗夫这个人物的严峻外貌是:说话粗鲁,语气傲慢,避开
“浪漫主义”的即一切诗情画意的属于心灵感受的东西。一八
六二年作者致函赫尔岑说:“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为理想人物
来描写,我不把他有何思想体系看得那么重要,我主要想把他
写成一条狼而又为他辩解——当然,这很困难,看来我没能做
到。”
巴扎罗夫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当作信仰,即使
这准则是多么受到尊重。赫尔岑把巴扎罗夫的这种虚无主义
归结为“完全、彻底摆脱了一切现成概念和陈规旧俗”。杜勃罗
留波夫进一步认同:“新人——他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对者,
因为唯心主义哲学把准则看成高于朴素的生活真理。”巴扎罗
夫对借抽象法得出的科学概念确无好感:“指的是什么科学?
泛泛的科学吗?科学一如手艺,有具体的门类,而泛泛的科学
是不存在的。”在此他只承认具体的科学,而把“泛泛的科学”
即哲学彻底否定了。他把哲学看成是“浪漫主义”哲学,腐朽,
胡说八道,与浪漫主义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认为巴扎罗夫的
思辩“从黑格尔的Allgemeinneit总体中得到了解放”。巴扎
罗夫认为人的行为不由抽象的、必须遵循的准则,而是由现实
生活决定的:“总的说来,准则是没有的,……只有感觉。一切
都取决于感觉。”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所奉准则的抗议也就
是民主主义者对唯心观的抗议。那时平民中的民主主义者按
杜勃留波夫说法“不但懂得,而且亲身感受到,世上绝对的东
西是没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对意义”,因此他们断然“摆
5父与子
脱开绝对理念而去接近现实生活,用他们的现实观替代一切
抽象概念”。
把小说《父与子》中发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该年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屠格
涅夫着重描写了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贵族
中较为进步和开明的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后者的代表则是
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作者选择了这样的
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说明,两种势力的较量乃是两个不同
阶级的对抗,“新人”巴扎罗夫用以反叛“先生们”、“老爷们”的
虚无主义带有直接反对贵族的性质。两者彼此仇视,仇视表现
在衣着、行为举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识层次。
巴扎罗夫初见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便为他那“妄自尊大、
拿腔拿调、纨绔习气”,“目空一切的架势”和贵族仪容而表示
反感,他以几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尔萨诺夫:“老古董!”
“人在农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
拿去展览!”而后者“贵族的秉性难于容忍巴扎罗夫的放肆”,
骂“这个医生的儿子,不单没有一点儿对长者的敬畏,甚至答
话有气无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争辩中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把自己说成是个热爱进步
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贵族”——“英国贵族”,“贵族
给予了英国自由并支持着这种自由”。可是巴扎罗夫不屑一
顾:“这种老调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因为在当时,英国之
于俄罗斯,相去何止天渊。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自由主义式
的爱民观点和改革,关于宪法、议会的美丽词句嗤之以鼻,他
6父与子
自己准备投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他为自己订下值得“巨人”
去做的任务,他要求积极的社会变革:“改造好社会,病根也就
清除干净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义者否定一切的历史必要性
时,并没有把虚无主义者提高到战胜贵族——“父辈”的高度,
即使在写巴扎罗夫和帕维尔·基尔萨诺夫雄辩式的争论时他
也没有完全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例如,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反
驳巴扎罗夫说,社会之所以取得进步不是由于否定,而是对
“文明成果”的肯定,虚无主义者仅仅是为否定而否定,他们好
比是生活在没有空气的真空里。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冲突看作
是两种社会历史势力的较量,而两者却都陷进了片面性误区;
冲突双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国知识分子的两极虽都了解和同
情人民和他们的需求,但在两者之上还有某个第三者——俄
罗斯人民,最后判断,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暂时还是个
“斯芬克斯”——谜。
超脱于两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严格地、客观地重视争
论双方的实际缺陷,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方能做到。我们不能断
言屠格涅夫完全属于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他确实把两派陷
入误区的纷争写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
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
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
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
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尼古拉·基尔萨诺夫
7父与子
就是一个富有诗感的人,他喜欢“让他悲喜交加的孤独思绪自
由翩跹”,他,“老浪漫主义者”,在花园里,在夜晚,当满天星斗
闪烁着的时候来点儿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
动了,可他那飘若游丝、穷不见尽的愁思在他心中激荡不散。”
至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他生来就不是浪漫主义者,他那
铁一样坚冰一样冷的带点儿法国厌世主义的心是不善幻想
的”,但就是这个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也有其人性内涵,他遇
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爱的激情的牺牲品,从
而不得不沉沦于“可怕的空虚”,失落于“无目的的生活”,他
“孑然一身,渐入黄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
惜、老之将至、青春不再的岁月”。
另一方面,作者赞赏“子辈”即虚无主义者的刚毅,反封建
的锐气,却并不赞赏子辈对美的冷漠,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尤
其对待浪漫主义激情、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
为历史所需的巴扎罗夫的否定一旦进入人的感情领域,
它就变得虚而不实,从而也导致了巴扎罗夫的自我矛盾。按书
中所说,巴扎罗夫“非常喜欢女性,喜欢女性美”,但“他把骑士
式感情当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
是“窈窕的身段”,与她们交往中想的是“愉悦”。可是巴扎罗夫
破坏了自己的理论,真心实意爱上安娜·奥金左娃了,他发现
自己身上就有为他原先所敌视的、与虚无主义者观点相悖的
浪漫主义,而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在和安娜·奥金左娃谈
话的时候,他用较之以前更为冷淡和轻蔑的态度对待一切浪
漫倾向,可当他独自一人时,一想起自己就有这种浪漫倾向不
由脑火。”巴扎罗夫把否定推到极限时,他的行为和感情反过
8父与子
来破坏了他的虚无主义,与旧的社会制度搏斗必不可少并行
之有效的否定,结果与人的感情和秉性不能适应。当此情况下
巴扎罗夫的“浪漫主义”个性开始显示了正面的人的自然属性
而不再屈从他的虚无主义了。
但是,他那虚无主义却又企图制止、支配他的感情流向,
于是两者的矛盾斗争导致了巴扎罗夫的个人悲剧。书中说道:
“他本可以轻易地平息血液的骚动,但他体内孕育着某种新的
东西,对此他从未允许存在过并曾有意地把它克制过,他的自
傲曾坚决反对过。”他用尽一切力量来压制自身的天性;结果
如何呢?情场失败后他戏剧性地承受着单恋的痛苦和委屈,失
去了内心的平衡,心灵的欢愉和工作的情绪。“工作的狂热劲
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苦苦的寂寞感,心绪不宁,他一举一
动都显得那样疲惫,甚至他行走时也不再是迈着那种坚实的、
勇往直前的步子。”巴扎罗夫说他自己在糟蹋自己并非出之偶
然,因为他曾嘲笑过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曾嘲笑过他的爱情
悲剧,然而他现在轮到自己感受爱情悲剧带来的伤痛。
巴扎罗夫的心灵危机也表现在哲学的和社会的悲观主义
中。他和阿尔卡季躺在干草垛旁出声想道:“我所占有的这一
小块地方比起广大空间来是如此地狭小,而那广大空间里没
有我,也与我无关;我得以度过的这个时段在永恒面前是如此
地渺小,而我到不了永恒,永恒中没有我……可就在这题原子
中,在这数学的一个点上,血液却在循环,脑子却在工作,有所
希冀……”人与自然不是相悖的对立关系,但在巴扎罗夫看来
却是两种绝然相反的力量。他在确认人的精神力量的同时,不
得不为自己依附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自然而哀伤。巴
9父与子
扎罗夫从哲学上的悲观主义,从他与自然界的心理隔阂,滋生
出他对后代人命运的冷漠。“举个例,”巴扎罗夫对阿尔卡季
说,“今天你走过村长菲利浦家他那白白的、漂亮小屋的时候
说,如果俄罗斯最后一个农民也能住上这样的小屋,那时俄罗
斯就达到完善的地步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促使它实现
……但我憎恨诸如菲利浦或西多尔这样的最后一个农民。干
吗我要为他们拼死卖力,他连谢也不说一声?……即使对我说
声谢,又值得了多少?他住上了白白的漂亮小屋,我则将老朽
入木,往后又怎样呢?”
不过,在小说《父与子》中,个人主义者与大自然隔阂而产
生的悲观,由屠格涅夫缝补了,承作者之力,在大自然面前的
人的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弥合。巴扎罗夫过早地夭折,死
于即将发生大变革的社会的门槛上,屠格涅夫在小说结尾处
描写了荒芜的乡村公墓,巴扎罗夫年迈父母无法消解的痛苦
之后,接着以强劲的抒情表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坚定
信念:“难道他们(指年迈的父母——译者)的祈祷、他们洒下
的泪水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真挚的爱并非万能?
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颗多么热烈的、有罪的、抗争的
心,墓上的鲜花依然用它纯洁无邪的眼睛向我们悠闲地张望,
它们不只是向我们述说‘冷漠’的大自然有它伟大的安宁,它
们还谈及永远的和解和那无穷尽的生命……”自然生命有其
多样性和无穷性,这是永恒的规律,屠格涅夫以此作为活泼、
乐观的结尾,让悲剧得到升华。在这里,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
起的悲剧,因认识到世界是个辩证地发展着的过程,因触摸到
强劲的、饱满的自然生命整体及它内部的和谐性,从而得到了
化解。
历来的学者们都认为,巴扎罗夫就其本质而言,是和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人”的种种社会—心理典型联系着的,是和时
代的主要意识倾向联系着的。确实,作者为塑造“民主主义者
总体形象”广泛搜集了生活素材,把观察所得预先记进日记,
用心注意着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扎伊采
夫及其他许多民主主义者的行为、观点。屠格涅夫与他们的交
往当然也有助于这篇小说的创作,不单单如作者自谦那样取
自“熟人德米特里医生”。作者力图通过巴扎罗夫创造出一个
六十年代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个典型代表最主
要的特征是全面否定一切。但这形象是如此地气势磅礴,以至
不为那个时代空间所限。屠格涅夫说他的巴扎罗夫的种种特
征不仅仅涵盖六十年代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写巴扎罗夫,把
巴扎罗夫包括在抱着“真诚地否定”的广大一群人之中,他不
仅把主人公和杜勃罗留波夫并排放在一起,也把他和别林斯
基、巴枯宁、赫尔岑等放在一起,从而他的认识价值超过了所
展示的那个年代。
随着历史的进展,巴扎罗夫的形象越来越变得复杂,当代
人论及屠格涅夫这篇小说的时候依然在不断争论,提出一个
接一个的看法,(至少我这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便是如此。)
看来,屠格涅夫确实成功地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国社
会发展的某些内在特点。
本文为原创文章,版权归旷野小站所有,欢迎分享本文,转载请保留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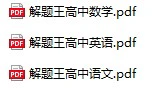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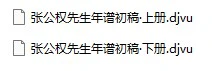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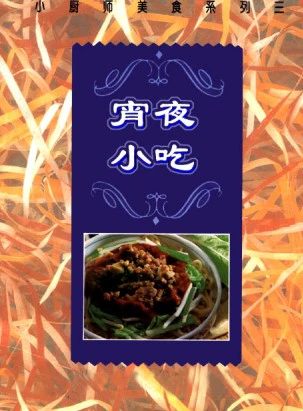

![群星《天碟落地》10CD [24b/44.1K]](https://www.z4a.net/images/2022/11/05/Cover.jpg?imageView2/1/w/375/h/250/q/70)

![高中数学-学魁解题妙招(PDF格式)[s519]](/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0000/20230213/089.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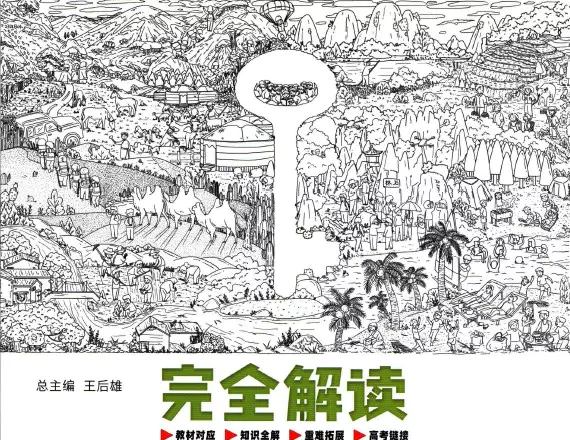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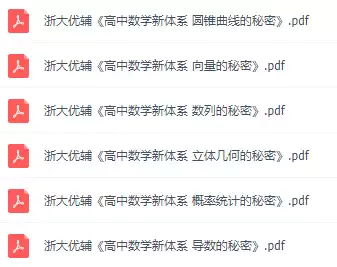
![2023新年新春兔年春节年会邀请函元宵节开工大吉年终总结PPT模板[s3040]](/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2/12202214/1221059/webp/1221059-t.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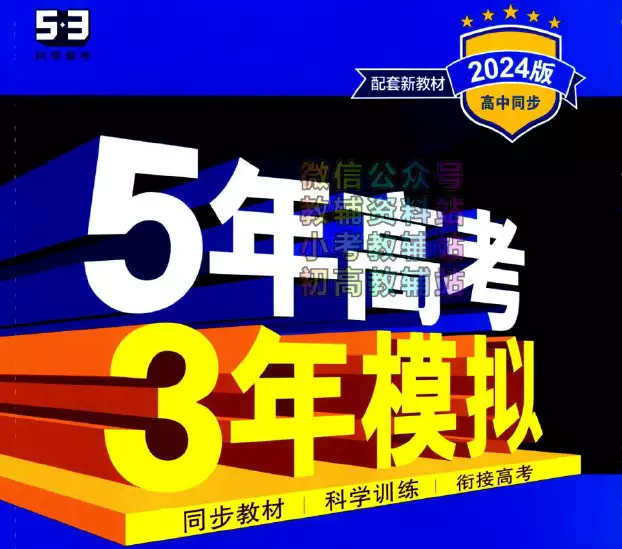
![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历年真题电子版及模拟试卷下载(含听力和答案解析 CET4、CET6试卷可打印)[s1697]](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3/0518/447/webp/001.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黄夫人物理(2024版)(pdf电子版下载)[s1361]](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2024/03/179.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圣经新译本》txt格式+epub格式+pdf格式下载(一生必读的60部名著)[s3465]](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2/09211059/0922013.jpg?imageView2/1/w/375/h/250/q/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