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浪花》(pdf电子书下载)[s2708]](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2024/05/21.webp)
1
三月的黄昏。
夕阳斜斜的从玻璃门外射了进来,在蓝色的地毯上投下
一道淡淡的光带。“云涛画廊”的咖啡座上几乎都坐满了人,
空气中弥漫著浓郁而香醇的咖啡味。夕阳在窗外闪烁,似乎
并不影响这儿的客人们喁喁细语或高谈阔论,墙上挂满的油
画也照旧吸引著人们的注意和批评。看样子,春天并不完全
属于郊外的花季,也属于室内的温馨。贺俊之半隐在柜台的
后面,斜倚在一张舒适的软椅中,带著份难以描述的,近乎
落寞的感觉:望著大厅里的人群,望著卡座上的情侣,望著
那端盘端碗、川流不息的服务小姐们。他奇怪著,似乎人人
兴高采烈,而他却独自消沉。事实上,他可能是最不该消沉
的一个,不是吗?
“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画家,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画商!如
果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最起码可以成为一个鉴赏家!”
这是他多年以前就对自己说过的话。“艺术”要靠天才,
不能完全靠狂热。年轻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只有狂热而缺
乏天才,他用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强迫自己承认这一点。然后
面对现实的去赚钱,经商,终于开了这家“云涛画廊”,不止
6浪花
卖画,也附带卖咖啡和西点,这是生意经。人类喜欢自命为
骚人雅士,在一个画廊里喝咖啡,比在咖啡馆中喝咖啡更有
情调。何况“云涛”确实布置得雅致而别出心裁,又不像一
般咖啡馆那样黑濛濛暗沉沉。于是,自从去年开幕以来,这
儿就门庭若市,成为上流社会的聚集之所,不但咖啡座的生
意好,画的生意也好,不论一张画标价多高,总是有人买。于
是,画家们以在这儿卖画为荣,有钱的人以在这儿买画为乐。
“云涛那儿卖的画嘛,总是第一流的!”这是很多人挂在嘴边
的话。贺俊之,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成为艺术家,却成
了一个很成功的,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最起码”!
“云涛”是成功了,钱也越赚越多,可是,这份“成功”
却治疗不了贺俊之的孤寂和寥落。在内心深处,他感到自己
越来越空泛,越来越虚浮,像一个氢气球,虚飘飘的悬在半
空,那样不著边际的浮荡著,氢气球只有两种命运,一是破
裂,一是泄气。他呢?将面临哪一种命运?他不知道。只依
稀恍惚的感到,他那么迫切的想抓住什么,或被什么所抓住。
气球下面总该有根绳子,绳子的尽头应该被抓得紧紧的。可
是,有什么力量能抓住他呢?云涛?金钱?虚浮的成功?自
己的“最起码”?还是那跟他生儿育女,同甘共苦了二十年的
婉琳,或是年轻的子健与珮柔?不,不,这一切都抓不住他,
他仍然在虚空里飘荡,将不知飘到何时何处为止。
这种感觉是难言的,也没有人能了解的。事实上,他觉
得现代的人,有“感觉”的已经很少了,求“了解”更是荒
谬!朋友们会说他:
“贺俊之!你别贪得无厌吧!你还有什么不满足?成功的
浪花7
事业,贤慧的太太,优秀的儿女,你应有尽有!你已经占尽
了人间的福气,你还想怎么样?如果连你都不满足,全世界
就没有该满足的人了!”
是的,他应该满足。可是,“应该”是一回事,内心的感
触却是另外一回事。“感觉”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不会和你
讲道理。反正,现在,他的人虽然坐在热闹的“云涛”里,他
的精神却像个断了线的氢气球,在虚空中不著边际的飘荡。
电动门开了,又有新的客人进来了。他下意识的望著门
口,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走了进来,夕阳
像一道探照灯,把她整个笼罩住。她穿著件深蓝色的套头毛
衣,一条绣了小花的牛仔裤,披著一肩长发,满身的洒脱劲
儿。那落日的余晖在她的发际镶了一条金边,当玻璃门阖上
的一刹那,无数反射的光点像雨珠般对她肩上坠落——好一
幅动人的画面!贺俊之深吸了口气!如果他是个画家,他会
捉住这一刹那。但是,他只是一个“最起码”!
那女人径直对著柜台走过来了,她用手指轻敲著台面,对
那正在煮咖啡的小李说:
“喂喂,你们的经理呢?”
“经理?”小李怔了一下:“哪一位经理?张经理吗?”
“不是,是叫贺俊之的那个!”
哦,贺俊之一愣,不自禁的从他那个半隐藏的角落里站
了起来,望著面前这个女人:完全陌生的一张脸。一对闪亮
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和一张小巧的嘴。并不怎么美,只是,
那眼底眉梢,有那么一股飘逸的韵味,使她整张脸都显得生
动而明媚。应该是夕阳帮了她的忙,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她
8浪花
确实像个闪亮的发光体。
贺俊之走了过去。
“请问你有什么事?”他问,微笑著。“我就是贺俊之。”
“哦!”那女人扬了扬眉毛,有点儿惊讶。然后,她那对
闪烁的眸子就毫无顾忌的对他从头到脚的掠了那么一眼。这
一眼顶多只有两三秒钟,但是,贺俊之却感到了一阵灼灼逼
人的力量,觉得这对眼光足以衡量出他的轻重。“很好,”她
说:“我就怕扑一个空。”
“贵姓?”他礼貌的问。
“我姓秦。”她笑了,嘴角向上一弯,竟有点儿嘲弄的味
道。“你不会认得我。”她很快的说:“有人告诉我,你懂得画,
也卖画。”
“我卖画是真的,懂得就不敢说了。”他说。
她紧紧的盯了他一眼,嘴角边的嘲弄更深了。
“你不懂得画,如何卖画?”她咄咄逼人的问。
“卖画并不一定需要懂得呀!”他失笑的说,对这女人有
了一份好奇。
“那么,你如何去估价一幅画呢?”她再问。
“我不估价。”他微笑著摇摇头。“只有画家本人能对自己
的画估价。”
她望著他,嘴边的嘲弄消失了。她的眼光深不可测。
“你这儿的画都是寄售的?”她扫了墙上的画一眼。
“是的,”他凝视她。“你想买画?”
她扬了扬眉毛,嘴角往上弯,嘲弄的意味又来了。
“正相反!”她说:“我想卖画!”
本文为原创文章,版权归旷野小站所有,欢迎分享本文,转载请保留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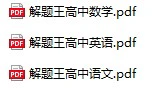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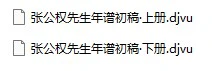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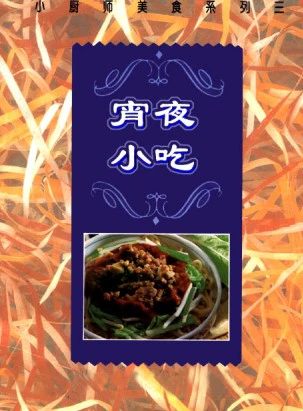

![群星《天碟落地》10CD [24b/44.1K]](https://www.z4a.net/images/2022/11/05/Cover.jpg?imageView2/1/w/375/h/250/q/70)

![高中数学-学魁解题妙招(PDF格式)[s519]](/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0000/20230213/089.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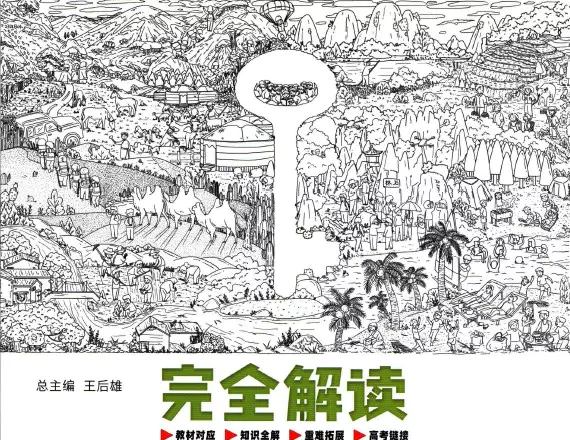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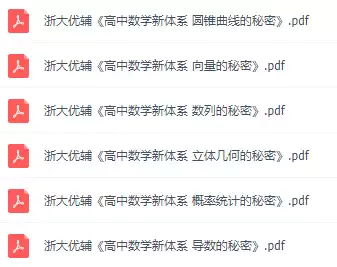
![2023新年新春兔年春节年会邀请函元宵节开工大吉年终总结PPT模板[s3040]](/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2/12202214/1221059/webp/1221059-t.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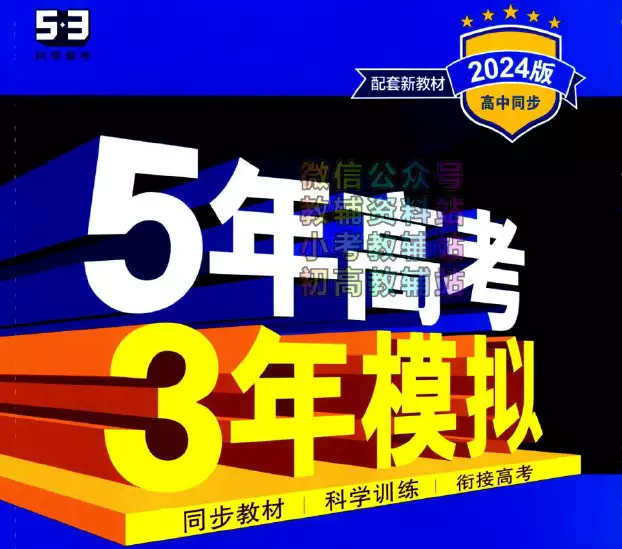
![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历年真题电子版及模拟试卷下载(含听力和答案解析 CET4、CET6试卷可打印)[s1697]](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3/0518/447/webp/001.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黄夫人物理(2024版)(pdf电子版下载)[s1361]](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2024/03/179.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圣经新译本》txt格式+epub格式+pdf格式下载(一生必读的60部名著)[s3465]](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2/09211059/0922013.jpg?imageView2/1/w/375/h/250/q/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