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加]南茜·休斯顿.陈蓁美译.译林出版社(2008)(PSD格式电子书下载)[s3406]](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2024/07/8.webp)
译序
陈蓁美
南希·休斯顿说她写作《断层线》的动机源于阅读吉塔·塞伦尼的《德国创伤》(Gitta Sereny,The German Trauma),以及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伤痕“Lebensborn”(生命之源);那是纳粹为了繁衍纯种日耳曼后代而建立的“种马场”,而繁衍的手段除了有计划地进行交配之外,还有在纳粹占领区窃取具有雅利安特征的孩童,再予以洗脑、教化。
不过,通往这个神秘过去的道路却绕了好几个弯。2004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与20世纪40年代住在欧洲的外曾祖母乍看之下并没什么关联。南希·休斯顿将全书分成四条脉络,分别由同一家族的四位小主人翁为出发点描述所见所闻与所感,让读者依序进入个性迥异、生活环境不同但却都是六七岁的索尔、杭达、莎荻、克莉丝汀娜这四人主观的世界,看他们如何在为一些乍看琐碎、互不相干的事欣喜或烦扰。四条脉络,前后呼应,环环相扣,故事的结束也是开端,而读者成了唯一可以拼凑事实原貌的全知旁观者。
所以读者从轻松、琐碎或天真的只字词组,越来越能感受到背后隐含的严肃、悲痛与深沉,而历史的洪流也许只是克莉丝汀娜家族史的背景。休斯顿更关心的是杭达为了知道“生命之源”的希伯来语而痛失好朋友大哭一场,令克莉丝汀娜没齿难忘的创痛只是得不到一个洋娃娃。读者因为“全知”,面对这种“侧写”的手法时,愈能升起无法抑制的悲恸之情。被纳粹偷来的克莉丝汀娜在纳粹家庭过着快乐的生活,休斯顿没有描绘纳粹家庭的残忍,反而惊心动魄地描述克莉丝汀娜与养母分离的场面。克莉丝汀娜得知自己不是波兰人时,第一件事是躲在浴室里唱着和小白花有关的歌,这是全书极为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这里,休斯顿超越了对“纳粹”、对“人类罪行”的指控,而指向更基本的“人类对立”与“文化认同”的荒谬。
对于喜爱历史、心理分析、对当代文学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断层线》是一座质纯量丰的矿山。译者特别想提出的是,休斯顿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描述一个“不可说”的题材时,仍不忘提出大胆的历史对照,譬如当代美国与六十年前纳粹的呼应。对于小索尔与希特勒的相似性,南希·休斯顿指出:“我相信美国正往法斯西主义移动,就某些方面来看,美国与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确有几分神似,让我害怕,不过我并非为了这一点而写《断层线》,我想借此书探索人性不可预测的一面:一个了不起的小孩可以变成庸才,一个有点古怪的小孩可以变成令人赞叹的大人。”
南希·休斯顿说她的老师罗兰·巴特一直很想写小说,但是往往为了决定人物的名字而停顿下来。而“名字”或“语辞”在《断层线》里是很重要的角色,暗喻人物的性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到德国慕尼黑旅行时,他觉得德语“就好像一道道大门在他面前关上,让他碰得一鼻子灰”。他发现菜单上列了许多worst(最糟糕)的菜,不过却写成wurst(德语“香肠”之意),他因而嗤之以鼻,并发愿将来有一天统治天下,第一个要实行的法律就是大家说英语。
不同于索尔对外语的排斥态度,索尔的父亲杭达因为学习希伯来语而发现“当每个东西有两种不同的名字后,世界变得不太一样”。学习希伯来语不仅让他心情愉快,更让他从中找到镇定的力量。后来他遇见美丽的阿拉伯女孩努姿哈,新语言混合初恋的滋味,对他更是充满魅力。语言的魅力恐怕与语言原本的意义无关了。杭达尽管口中跟着努姿哈复诵除咒语,心里却翻译成:“努姿哈,你有世上最美的眼睛,我疯狂地爱上了你。”当杭达被周遭局势扰得无所适从、头痛欲裂时,他“开始在卧房里旋转,作出飞机要坠毁的样子,并说:‘ROCH,ROCH,ROCH HA-CHANAH。’在这个游戏里,ROCH指头,HA-CHANAH是爆炸(其实ROCH HA-CHANAH为希伯来语‘一年的头’,也就是新年之意)”。
杭达的外婆爱哈小时候则有太多的“名字”。她原本在德国家庭快乐生活,以为自己名叫克莉丝汀娜,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是养女,她的生活开始变调。后来她遇到来自波兰的尤安(原来的波兰名字为亚内克),两人一起探索自己的身世,尤安猜测她真正的名字可能是克莉丝蒂纳或克莉丝特卡。尤安告诉她,她和他一样是窃童,他们住在敌人家里,说他们的母语已经被连根拔起,叫她不能再唱德语歌。她跟着尤安学习波兰语,准备与波兰家人团聚。战争结束,一位美国人却告诉她,她其实是鸟克兰人,她真正的名字是克拉丽莎。大惊失措的她,原以为自己会回鸟克兰与家人团圆,最后却送往加拿大,被克莉斯瓦堤夫妇收养。
心神不宁的杭达借由语言发明战争游戏,而从一堆名字里仍然找不到自己是谁的爱哈似乎把“名字”的多样性看得更轻松、自由。当她问女儿莎荻“什么是Hamburger”时,莎荻时而回答“汉堡”,时而回答“住在汉堡的先生”。有一次杭达和爱哈的女友梅赛德斯玩文字图像游戏,爱哈说:“只有跟梅赛德斯说同一种语言,她的魔法才行得通。如果她说的不是死乌鸦而是Cuervo muerto(西班牙语死乌鸦之意),杭达什么也看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纯音演唱:大家都听得懂,我的歌曲完全透明……”爱哈想借由舍弃歌词、名字,打破语言的界限?消弭语言造成的隔阂、误解或谎言?杭达的母亲莎荻一直以为自己和名字一样的“悲伤”(sad),却不知莎荻(saddie)其实是犹太语“公主”之意。沉浸在学语言的乐趣中的杭达,却也因此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他忘了除咒语避开努姿哈的毒眼,导致母亲莎荻发生车祸,永远残废(杭达自已是这么认为的)。长大后的杭达变成支持美伊战争的好战分子,企图杀光阿拉伯人…..
《断层线》里对立、误解、谎言、冲突林立,却始终温柔缭绕,虽然有时轻如薄雾但是不曾消失,这种“温柔”是我个人阅读这本书时很特别的感受。当我读着“狂妄”的索尔、“焦虑”的杭达或“忧愁”的莎荻时,仍然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温柔,这种感觉很奇妙,因为字面上是看不到的。
南希·休斯顿是目前国际文坛上用英语与法语两种语言写作的双语作家的翘楚,但她在法国文坛所受到的重视似乎胜过英美文坛;她在法国名列畅销作家之林,然而英美文坛仍不知道该如何归类她的作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法双语文学曾在巴黎交会并擦出灿烂的火花,当时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以法语创作《等待戈多》,成就文学经典。南希·休斯顿承续这条路,以双语创作与翻译,虽然还未能像前辈贝克特那样受到英语文学评论界应有的重视,不过已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个现象。我们相信南希·休斯顿的才华势将受到更广泛的肯定。
《断层线》荣获2006年法国费米娜奖,而当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文学奖则颁予《复仇女神》。两书主题都与纳粹罪行有关,二位作者都以英语为母语。这是因为法国的文学奖特别慷慨,还是因为非母语写作能展开更宽宏的视野?南希·休斯顿说:“唯独语言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唯独母语的伪天性被废除时,我才找到要说的东西。”《断层线》译成二十种不同的语言,却迟迟未在美国发行①,个中原因,相信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一些答案。
①《断层线》首先以英语写成,不过休斯顿的美国出版商希望修改内容,直到今天中文简体版出版之时,仍未在美国发行。加拿大2007年发行英语版,入围加拿大罗杰斯作家基金会小说奖(Rogers Writers'Trust Fiction Prize),2008年在英国发行,入围奥兰治奖(又译橘子奖)。
本文为原创文章,版权归旷野小站所有,欢迎分享本文,转载请保留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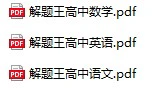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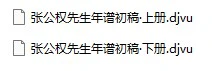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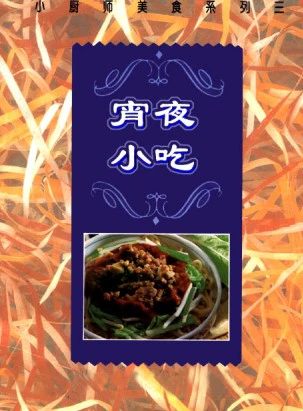

![群星《天碟落地》10CD [24b/44.1K]](https://www.z4a.net/images/2022/11/05/Cover.jpg?imageView2/1/w/375/h/250/q/70)

![高中数学-学魁解题妙招(PDF格式)[s519]](/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0000/20230213/089.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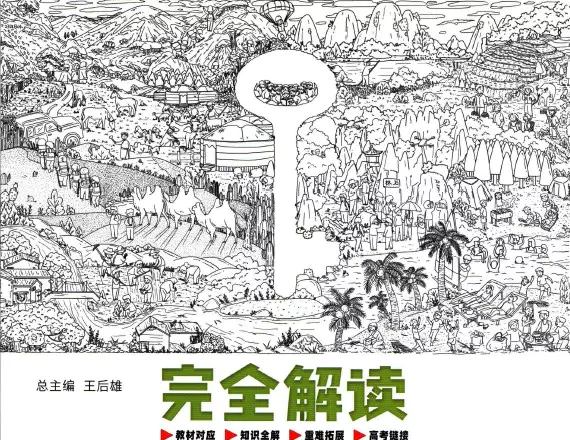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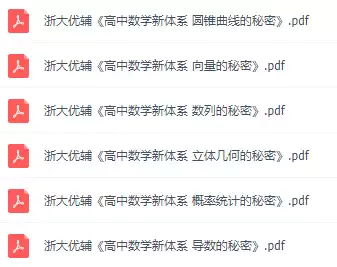
![2023新年新春兔年春节年会邀请函元宵节开工大吉年终总结PPT模板[s3040]](/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2/12202214/1221059/webp/1221059-t.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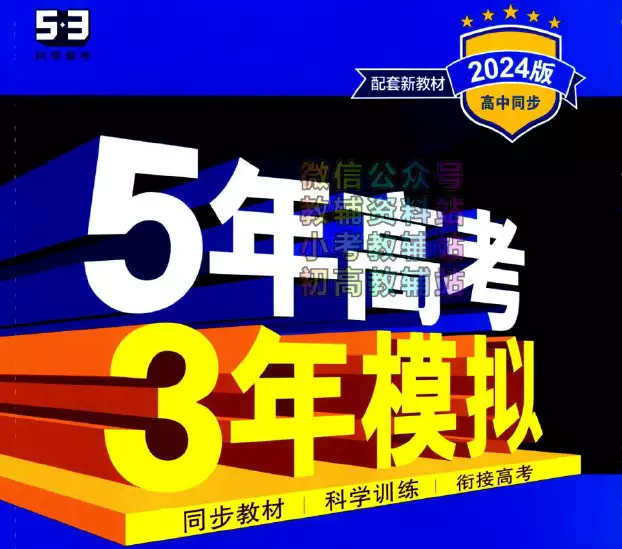
![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历年真题电子版及模拟试卷下载(含听力和答案解析 CET4、CET6试卷可打印)[s1697]](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3/0518/447/webp/001.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黄夫人物理(2024版)(pdf电子版下载)[s1361]](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2024/03/179.webp?imageView2/1/w/375/h/250/q/90)
![《圣经新译本》txt格式+epub格式+pdf格式下载(一生必读的60部名著)[s3465]](https://www.123ppp.com/wp-content/uploads/data_123ppp_com/2022/09211059/0922013.jpg?imageView2/1/w/375/h/250/q/70)